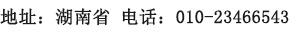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民族融合加剧。但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比较活跃,突出表现为玄学的兴起、佛教的输入、道教的勃兴以及波斯、希腊文化的渗入。文化交融与学术思想趋于活跃,为版本学的孕育和成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一般认为,版本学正式确立于宋代,但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版本学的最终确立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积累,是中国古籍版本学史无法跨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一、魏晋南北朝的同书异本现象同书异本现象的广泛存在是版本学得以孕育和发展的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因文献生产方式的改进、佛经的翻译和流传、官私校书注书的兴起,以及图书剽窃、作伪等因素的影响,同书异本现象较之前代更加普遍。纸虽在东汉就开始运用于书写了,但最初并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简策仍是当时图书的主要形式。入晋以后,纸用作书写材料渐而普及。纸的地位的变化,使得文献生产复制变得更加容易,也加剧了同书异本现象的产生。这从文献记载就可以看出来,如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大量出现“江南本”“江南旧本”“河北本”“古本”“俗本”“误本”等。因同书异本现象的大量涌现,版本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人们因版本选择之误,闹出来的笑话也不断,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如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载: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捐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缪,误反“颛顼”字,顼当为许录反,错作许缘反,遂谓朝士言:“从来谬音‘专旭’,当音‘专翾’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误焉。[1]
佛经的翻译和流传也导致了大量同书异本的产生。早期佛经的翻译,主要是通过口授,也有一人传言、一人笔受的对译,翻译方法多为直译。经卷的选择没有系统性,随意性较大,且重复翻译较为常见,因而极易产生同书异本。这主要是因为“经出西域,运流东方,提挈万里,翻转胡汉。国音各殊,故文有同异;前后重来,故题有新旧。”[2]至南朝梁释僧祐时,“或一本数名;或一名数本;或妄加游字,以辞繁致殊;或撮半立题,以文省成异。至于书误益惑,乱甚棼丝,故知必也正名,于斯为急矣。”[3]僧祐对佛经的同书异本现象多有记载,如卷七《又别剡西台曇裴记》云:“此经凡有四本,三本并各二名,一本三名,备如后列。其中文句参差,或胡或汉音殊,或随义制语,各有左右,依义顺文,皆可符同。所为异处,后列得法利、三乘阶级人数,及动地、雨华、诸天妓乐供养,多不悉备,意所未详。”卷八又载:“《放光》《光赞》,同本异译耳。其本俱出于阗国持来,其年相去无几。”
鸠摩罗什翻译佛经(图片来自网络)因同书异本的增多,“广勘异本,择善而从”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也促进了版本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社会虽然动荡,但官私校书不断。任昉(彦升),乐安博昌人,《梁书·任昉传》称其“坟籍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昉卒后,高祖使学士贺纵共沈约勘其书目,官所无者,就昉家取之。”王僧孺,东海郯人,亦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勘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媲美。阚骃,字玄阴,敦煌人,史载其“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十余卷。”[4]
与私家校雠相比,官方校书成绩更大。刘宋间,秘书丞殷淳(粹远)、谢灵运、王俭都先后在秘阁校订坟籍。齐沈约(休文)也曾在东宫“校四部图书”[5]。梁任昉(彦昇)任秘书监,时“秘阁四部,篇卷纷杂”,他“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6]。北魏孙惠蔚(叔炳)入东观,曾上疏请“臣今依前丞相卢昶所撰《甲乙新录》,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其省先无定本,广家推寻,搜求令足。今求令四门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精校考,参定字义。”[7]北齐天保七年(年),诏令樊逊、高乾和、马德敬等12人校定群书。而要刊定众籍,必须广集众本。于是樊逊建议:
按汉中垒校尉刘向受诏校书,每一书竟,表上,辄言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太史公、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较,然后杀青。今所雠校,供拟极重,出自兰台,御诸甲馆。向之故事,见存府閤,即欲刊定,必藉众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书辛术、司农少卿穆子容、前黄门郎司马瑞、故国子祭酒李业兴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8]
樊逊等通过借私人藏书来校订官府藏书,共得别本余卷,《五经》诸史的各种版本网罗无遗,堪为广罗异本的典范。
魏晋清谈场景(图片来自网络)魏晋代汉,异端思想纷起,儒家独尊的地位岌岌可危。期间老、庄活跃,玄谈风行,辨言析理,清要为贵,表现为抽象的理论比较发达,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层出不穷。王弼、韩康伯注《周易》、何晏注《论语》、杜预注《左传》、范宁注《谷梁传》、郭璞注《尔雅》《庄子》、韦昭注《国语》、徐广注《史记》等,是这一时期注疏家的代表,亦都考察异同,择善而从。如何晏(平叔)《论语集解》自序曰:“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之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说,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9]晋末徐广(野民),东莞姑幕人。晋孝武帝以广博学,除为秘书郎,校书秘阁,作《史记音义》,多采异本,注异同。《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有“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句,徐广注曰:“‘盟’,一作‘明’”,此为注异字例;再如有“且《盘庚之诰》有颠越勿遗,商之以兴”句,徐注云:“一本作‘《盘庚之诰》有颠之越之,商之以兴”[10],此为注异文例。故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序》云:“(《史记》各本)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辨其实,而世之惑者,定彼从此,是非相贸,真伪舛杂。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研核众本,为作《音义》,具列异同,兼述训解。”[11]
南北朝间因注书而事校雠的,以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裴骃撰《史记集解》、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为代表,也是广集诸书,参研同异,对异文、脱文、错字及讳字等有所说明。如注异文例,《三国志·魏书·崔琰传》有“刚断英跱”,裴案:“‘跱’或作‘特’,窃谓‘英特’为是也。”《世说新语·文学》“孙子荆除妇服”条,有“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句,注:“一作‘文于情生,情于文生’。”如注误字例,《三国志·魏书·徐晃传》“今假臣精兵”,案:“晃于时未应称臣,传写者误也。”[12]《世说新语·赏誉》“王右军道东阳”条有“我家阿林”句,注:“‘林’应作‘临’。《王氏谱》曰:‘临之字仲产’。”如注脱文例,《世说新语·文学》“僧意在瓦官寺中”条有“僧意云:‘谁运圣人邪?”句,注:“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庆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义。然王修善言理,如此论,特不近人情,犹疑斯文为谬也。”[13]裴骃撰《史记集解》,博采贾逵、服虔、王肃、杜预、韦昭、徐广等家注本及异文。如《宋微子世家》:“曰‘太师,少师,我其发出往?吾家保于丧?”《史记集解》注曰:“徐广曰:‘一云‘于是家保’。’骃案:马融曰‘钦大夫称家’。”[14]以上注文中“或作”“一作”“诸本”“一云”等词,都是他们广勘异本的明证。
此外,因剽窃、作伪等因素,也导致了同书异本现象的产生。据《世说新语·卷上·文学第四》载:“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15]郭象剽窃了向秀的成果,仅自注了两篇,其余只是定点文句,稍加改易而已。从文本内容看,向、郭两人的《庄注》实乃同书异本。又据《梁书·萧琛传》载,萧琛在宣城为太守时,“有北僧南渡,惟赉一葫芦,中有《汉书序传》。僧曰:‘三辅旧老相传,以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书多有异今者,而纸墨亦古,文字多如龙举之例,非隶非篆,琛甚秘之。及是行也,以书饷鄱阳王范,范乃献于东宫。”皇太子命刘之遴、张缵、陆襄等人参校异同,刘之遴具陈异状十事,其大略曰:
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次《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杖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16]
此所谓“班固真本”,据宋人王之望推断,当是伪本。由以上所举,可知当时的学术界对同书异本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