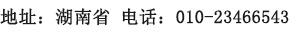三位黄冈老乡,中为刘不朽,右一为郭寒。
人间如隙,时光如驹。俯仰之间,刘不朽老师离开我们已快一周年了。玉露凋伤的季节,他驾鹤西去,恍若飞鸿踏雪泥,但世事并不尽如烟,这些日子,每思及不朽老师的桩桩旧事,忆及《长相忆》系列文章的文采风流,些些旧影,如在目前,般般陈迹,涌上心间。
先说几句题外话,《左传》上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是刘不朽先生名字之由来,也是他毕生遵循的人生美学。以立言论,刘老年即开始文学创作,年推出首部诗集《山寨水乡集》(合著),直至逝世前一个月,仍然笔耕不辍,创作、著述垂六十年。其间虽因各种原因中辍写作,但他一直未尝忘怀“诗是吾家事”这一初心,用坚实的足迹丈量着三峡,采集民风,采撷诗情,推出了一本又一本的诗集,如《歌满山乡》、《山之韵》、《三峡之恋》、《三峡梦三峡潮》等等,可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一位真正的三峡歌者。不朽老师的这些诗集,大多都给我送过,但如果在冷摊遇到,我也会购来,请他在书上题字。有一天,我带去了出版于的他的《金翅鸟》长诗集,他感慨不已,在扉页手录了一首旧作相赠:“人生路上几多山,做人更比做诗难。做诗只忌随人后,做人最怕上人前。十年面壁谁知苦,一朝成名众眼馋。但求人品如诗品,不畏人言敢立言”,题毕,他给我细述写作这首诗的背景,并说这是他多年人生阅历的体悟,是可以作为座右铭的。是的,细细揣摩这首诗,浸透了人生的百味,却也达观其外,这不就是立德吗?
版面留珍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毕业后分到宜昌,那时就知道刘老是我的广济老乡,是全国有名的乡土诗人,但初来乍到,我并没有冒昧地去打扰他。过了几年,我才鼓足勇气走进了解放路2号刘老的办公室,他倒履迎接我这个不速之客,并主动题赠了几本诗集给我。可以说,这次拜访是我们的首次见面,但后来因工作繁忙,交集无多。年,报社安排我主编副刊,后来又打理作协的日常事务,与刘老的交往渐渐地多了起来,年,还应邀参加了他的新书《三峡探奥》的研讨会。记得在年,为打捞宜昌老一辈作家诗人的创作记忆,我设想开辟“宜昌作家档案”专栏,并首先上门约请刘老撰稿,他听说后十分支持,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翻找散落在各处的故纸,整理心中数十年来的那些创作碎片,写成近五千字的《我的文学创作历程》一文。在这篇回忆文章中,他把自己的文学创作分为五个时期,从在广济老家读私塾,到考入广济县中,后离开学校选调入伍,在部队度过九年的军营生活,其间大量读书,萌发强烈的创作欲,并发表了处女作,这是“处女期”;年到年,转业到宜昌,习诗不辍,在全国大刊上发表诗作,推出诗集,到北京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是成名的“青春期”;文革期间遭受批判,下放五七干校,这是“磨难期”;年起至离休,重新唤发青春,创作题材广泛,质量较高,是创作的“成熟期”,离休后费多年功夫写《三峡探奥》,是其收官之作,也是“隐居期”。当时只道是寻常,正是那时的一个想法,让刘不朽老师有机会思考和整理跨越半个世纪的丰富人生,如今看来,这是一篇弥足珍贵的创作总结。正是它,让我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萌动着请刘老亲撰回忆录的念头,一有机会,我就把这个想法直接向他表达出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年春节后,我带上武穴土产山药和酥糖,上门给不朽老师和武金兰老师拜年,他终于主动提出,年后即可给晚报写回忆专栏了,我大喜过望,由此,也开启了我与刘老最后两年的“蜜月期”。
三峡晚报报道的刘不朽先生逝世版面
至今还保存着最后两年与刘不朽老师的来往短信。值得一说的是,当很多老作者晚年乐于上网并乐此不疲时,他对网络一直保持着警惕,坚持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