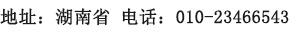医院里将“心理护理”发挥到极致的一个科室了。护理站总是有接踵而至的预约患者,科室走廊里驻足的除医护人员外就是患者及家属了,病房里要么喧嚣嘈杂要么鸦雀无声,仿佛总是难以达到一种祥和的平衡感。而我每日穿梭在这样的环境中,除了近距离地体会抑郁患者的无助、焦虑患者的不安、木僵患者的痛苦……还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感知到爱的涵义。
来到精神卫生科的第二周,我见到一个亚木僵的女孩,出乎我的意料,她竟然是一名大二的护理学生,入院那天,她目光呆滞,少语少动,长达四十分钟的问诊未能使她开口说一句话,连基本的眼神交流都没有,所有的病史都是由其父母和姐妹所提供。我看着眼前的这个花季女孩,好想听她亲口诉说她所遭遇的一切,哪怕大声地痛哭一场也无妨,但这个夙愿在此刻显然是一种奢望。随后的20天时间里,我每天都会去病房看望她,或许是带着一种对学妹关怀备至的初衷,我和她交流的内容大抵都是大学生活、对于护理专业的理解以及未来的规划。起先完全是我一个人在说,她与我基本没有眼神的交汇,连基本的点头摇头都不曾回应我,连着两周都是如此,我也在与她说话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感和挫败感。
我查阅了有关亚木僵护理方面的文献,发现除了基础护理、安全护理之外,心理护理的内容大多都是“获取患者的信任,给予充分的尊重,引导患者面对现实”,但有关亚木僵的个案护理却是少之又少,我在想,如何才能实现心理护理的个体化?
随后的一段时间,我尝试着与患者家属进行交流,交流的内容是患者的性格特点、爱好习惯、以往和家人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患者虽然少语少动,但意识清晰,听到我们对话内容时偶尔会有眼中噙泪的表现。或许这样间接的方式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我还尝试着自己制作附带图文的明信片以鼓励她,将她所喜欢的照片剪辑成视频播放给她看,把我在大学时期的烦恼以及各种应对方法一一讲给她听,每逢去病房看她的时候都会给她播放一些舒缓轻柔的轻音乐,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些有没有在某种意义上带给她些许慰藉或者是帮助,因为她的疾病转归并没有想象地那么显而易见。
住院的第四周,当我拉着她的手问她想不想回家时,她竟然看着我说想,那一刻我好像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这么久的努力终于换来了一次她的注视和回应。这一天好像是一个时间节点,于我于她都是,我在暗自高兴的同时也庆幸她的病情有了质的好转,随后的一周时间里她回应我的次数越来越多,饭量也渐渐趋于正常。尽管在出院时仍然没有恢复到正常的模样,但却已经大有好转了。女孩长达二十几天的住院治疗,我想或许药物治疗和专业心理治疗师的个体治疗都是其疾病康复的重要因素,但我的努力或许也为其增添了不少助力。
我想,心理护理大概就是尽可能地感知患者的无助与痛苦,以一种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去和他们沟通,以一种包容理解的眼光去对待他们,不可否认的是,世界上从来都没有感同身受,无论我们做的看起来有多么完美,但是常常会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不过,正如特鲁多医生所言: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医学是伟大的同时势必也是局限的,它在极大程度地体现温度的同时也必然会夹杂着距离感。未来,我们所能做的还有很多,我想心理护理大概是将医者与患者连在一起最为奇妙的纽带。
本期主播:刘爽,女,硕士在读,山西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