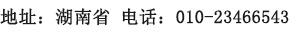原创王慧明39深呼吸收录于话题#仁心12个
▼
何晓顺
医院副院长、广东省器官捐献与移植免疫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山大学器官捐献与移植免疫研究所所长。从事器官移植临床与科研工作33年,在无缺血器官移植、多器官移植及器官捐献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和原创性成果。
VOL.
作者|王慧明
摄影|陈家颖
编审|汪杨明辛欣
编辑|廖颖瑶
本文共字,阅读时间12分钟
60岁的严金贵曾经与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掀开上衣,他腹部有一个脸盆大小的“人”形伤疤,这是他刚接受完肝脏移植手术后的疤痕。待恢复健康后,严金贵说自己身体里承载着另一个生命的馈赠,必须活得更健康、更有意义,才是对身体里捐献者的尊重与感恩。
自从年我国尝试第一例肝移植手术后,根据中国肝移植注册年度报告显示,我国肝移植累积总数已超过2万例,不仅是肝脏,器官移植手术已成为挽救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重要医疗手段甚至唯一手段。《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曾撰稿称“器官移植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它为医学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什么是器官移植?通俗来讲,器官移植,是指将健康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个体内,并使之迅速恢复功能的手术。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在现代医学领域中,可以用于移植的不再局限于器官(例如心脏、肝脏和肾脏),同时也包括细胞和组织移植(例如造血干细胞、皮肤移植)。
在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一院)五号楼9楼,门口沉默地坐着等待探病的人群,他们眼中或充满希冀或暗淡无光,一门之隔的病房里面,住着他们的亲友,要么已经重获新生,要么生命正处于倒计时,随时可能被叫停。
这里是器官移植病房,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几家拥有所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疗中心,作为学科带头人的何晓顺,30多年来一直与“死神”较量,一次次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
◎何晓顺教授畅谈行医感悟。
1
入行
“我一直相信勤能补拙。”
8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大潮已汹涌澎湃,一批有理想有冲劲的年轻人纷纷离开自己的“铁饭碗”南下逐梦,从安徽医科大学毕业,工作3年后,何晓顺决定顺应时代潮流,南下去改革开放的前沿地追寻梦想。
同一时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作高级访问学者的黄洁夫决定回国,入职中山一院后,准备招揽人才在肝移植上大干一番,“初来乍到”的何晓顺因连续上交两篇手写综述引起了他的注意。“那时还在读研究生,学校当时的要求就是半年时间将课程全部学完。进入临床,我‘私下’跑到图书馆里一次次查找文献,交了两本厚厚的综述给黄老师,黄老师觉得我挺认真自觉的,就让我去他团队里帮忙。”
说起当年的因缘巧合,回忆24岁时的青涩模样,何晓顺眯了眯眼,不禁生出无限感慨,“我一直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天赋,但我一直相信勤能补拙。”
◎在何晓顺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放着30年来他在器官移植领域获得的各类成绩。
但彼时,这个被列入到20世纪人类医学三大进步之一的器官移植,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却“水土不服”,陷入了长时间的彷徨与停滞。由于术后缺乏有效的抗排斥药物、器官保存液体及受到相关技术制约等因素,从年到年间,全国肝移植手术仅做了58例,90%的患者在术中或者术后3个月内死亡,最长的患者也只存活了天,一连串失败的打击、加上技术的高难度、天价的费用……让当时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生们望而却步。
继续开展肝移植,意味着一切要从头开始,先要进行大量动物实验。“那几年,条件非常艰苦,每个人待在实验室里周而复始地和动物‘打交道’,往往一做就是一个通宵,我当时年纪小,还当起了饲养实验室动物的工作,也有师兄受不住,中途选择退出……”年轻的何晓顺渐渐地成为了器官移植团队的核心成员,年,时隔十年肝移植技术终于迎来曙光,在黄洁夫教授的带领下,中山一院器官移植团队完成了全国首例体外静脉转流下的肝脏移植。
◎年发表在《中山医科大学学报》上的手术报告(节选)。/《中山医科大学学报》截图
这台手术的技术水平实现了重大突破,无论是手术方式还是术后处理方式,均与当时的国际水平不相上下。手术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业内同行的信心,此后,国内肝移植手术进入到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直至年,中国肝移植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
突破
“每一次技术创新,都来自患者临床迫切的实际需求。”
28岁的许丽费了些力气才说服母亲同意她的选择——接受多器官移植手术,一次性切掉肝、胆、脾、胰、胃、十二指肠等9个上腹部组织器官。
事实上,她已经别无选择。年5月,她被断言,生命最多还能靠白蛋白输液维持几个月,医院甚至拒绝对她继续收治,自从被确诊为胰腺囊腺癌合并多发性肝转移后,许丽医院、药品和恐惧之间,但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死亡的逼近,还是第一次。
“豁出去了”许丽心一横,“既然都已经被‘判了死刑’,自己这么年轻,不试就什么都没有了。”彼时作为她信心支撑的,是她在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山一院器官移植科全国手术量位居前列的一则新闻。
当时器官移植技术在国内相对成熟,中山一院移植患者的生存率排在全国前列,但即便如此,摆在主刀医生何晓顺面前的却是一道极难的题,多器官移植是器官移植领域最为复杂的尖端技术,当时全球仅有数十例报告,绝大部分手术是在美国匹兹堡和德国的大型器官移植中心进行。“在此之前,国内也有人尝试过多器官移植,病人没出ICU就不幸离世了。”何晓顺说,为了降低感染的风险,他一头栽进了实验室中,从改良动脉静脉重建、预防胆道并发症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操作演练后,一种从未有过的“简化式的多器官移植”手术方式初具雏形,事后证明这种手术方式不但能有效缩短手术时间,也可显著减少移植患者的创伤与术后并发症出现。
◎年6月4日,广州本地媒体详细报道了这一例手术。/羊城晚报
虽然术后两年,许丽还是因为肿瘤复发离开了人世,如今回忆起多得的这两年时光,许丽的母亲依然充满感激,“我们学会了珍惜,挺好!”
今天,中山一院不但成为实施简化式多器官移植例数全球最多的中心,术后患者5年生存率也达到了75.4%。何晓顺感慨道,器官移植手术和其它手术的最大不同在于,如果不做,患者连一丝丝活命的机会都没有,与此同时,因为供体器官短缺,每一次手术机会都显得弥足珍贵,为了提高一点点移植成功率,医生们绞尽脑汁,如履薄冰。
年7月23日,在器官移植手术室内,何晓顺刚完成了世界首例“无缺血”肝移植,在护士的帮助下脱掉了沾血的手术衣。
◎何晓顺的这一创新成功破解了器官移植的世界性难题。/中山一院